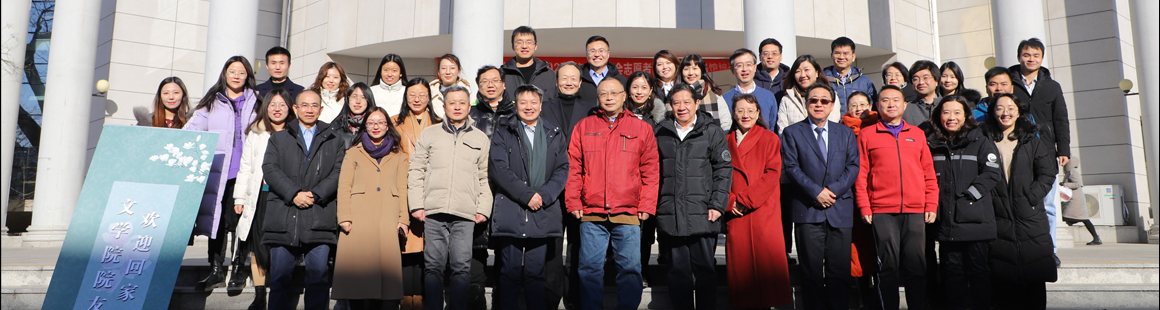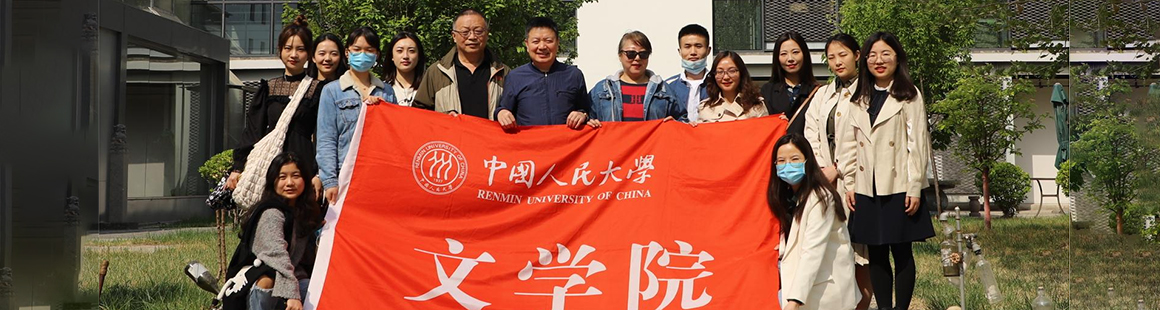【回忆录】人大中文83之碎片
发布时间:2010-05-31
来源:校友
人大中文83之碎片
郑学锋
写下这些文字,是为了记录这一段生命。如同潮水退后,拣拾沙滩上的贝壳海藻,它们或许不太夺目,但跟随潮水这一路走来的历程,深深地烙印在它们的生命里,永远不会被销蚀……
“先行者”
我是从一个鄂东南小镇走入人大的,虽然父母都是国家干部,但因为孩子多,那时候的收入不足以供给三个孩子念书,所以外祖母和父母亲还养了些家畜贴补家用。上大学的那天,我穿着雪白的的确良衬衫和爸爸一起离开家门的时候,已经工作了的哥哥拍了拍我的樟木箱子,羡慕地对我说:“老二,你是背着半头猪上北京的!”
多年后我一直记着这句话,我还记得他和我告别时的眼神,那里面有手足之情更有神往之心。他比我聪明,高考差一点分数就没再复读,毅然参加工作汇入社会洪流中了,可能没想到高考之门真的能被我们兄弟撞开,我的录取让他有了新的责任。20多年以来,每每我接到他的电话和信件时,我都几乎对他有求必应,不仅仅是因为兄弟,更多的是因为这句沉甸甸的话。
被录上北京的大学是我们家族的惊喜,以至于后来当我弟弟、堂兄、堂弟、侄子、外甥等等先后拥进武汉、上海、北京等地著名高校的时候,他们每每都会称我为“对家族最有贡献的先行者”。我知道,我是幸运的。
317
先行者亦即所谓“开先河”者,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之余,还有不少茫然无措举目无亲披荆斩棘开天辟地的苦恼和艰辛,这种心理准备在离开武汉登上北京的火车上还没有,因为那时候爸爸还在身边,通红的大学录取证书还揣在胸口没被新生报到处的老师们收走,但两天以后爸爸离开北京时,我感到了一些怯懦和惶恐,如同孩子误入了深山。
我的宿舍是人大学一楼317,那是一个陌生而躁动的环境,同学们来自天南地北,生活习性五花八门,光口音在我们宿舍就有四五种,一些从没听过的名词和不理解的生活方式搞得我晕头转向:港台歌手除了邓丽君还有我不知道的刘文正、甄妮;内蒙有些地方居然几个月洗一次澡;我是米饭吃不够馒头一个吃不完北方人居然说米饭吃不饱;还有牛奶葡萄酒要酸了才喝还美其名曰酸奶干白……
要习惯这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很庆幸有自己较强的适应能力,以至于很快就跟着马彤学会了“哥们儿”、“倍儿棒”之类的京腔并和大家打成了一片,而在每个宿舍里面安插一个北京的学生是我们辅导员老潘(这的确是我们的呢称而非大不敬)的良苦用心,我疑心他使用了当年毛委员提倡红军在基层连队建立党组织的招数,因为新生运动会和郊游时的迅速融合使大家都体会到了这一点。
我的宿舍窗户是朝南的,窗户底下是一个小花园叫紫藤阁,面对的是学二楼宿舍,因为那时候大学都是男女混居一楼(这一点让后来的师弟师妹们艳羡不已),所以四年的很多时光我都是在看著窗外度过的,那里有追逐打闹,也有爱恨情仇,有醉酒高歌,也有相看泪眼。记得最后一个初夏,毕业离校前两天,我和于水曾经一人抱着一瓶“佐餐”葡萄酒(那可是我们当年的XO)在那里彻夜长聊,远到将来带孩子去长白赏雪江南看花,近到毕业离校前把剩下的粮票再换几个鸡蛋把最后的情诗面交新闻系的小妹妹……我记不清是醉着回去的还是醒着回去的,但一个细节很清晰,就是我在醉意朦胧时分感觉到除了寒冷以外脸上很湿,我不知道是清晨的露水还是黑暗中的泪水。
“夜游神”小乐队
大学的幸福时光是和音乐联系在一起的。
那时候如果有卡拉OK,我坚信我们之间一定能出来一两位叱咤校园歌坛数年的人物,这里的“我们”是指“夜游神”小乐队成员:马彤、王勇、宗金柱、于水、傅兴志和我。当年的这支小乐队至少是在学一楼小有名气,因为它的霸气和前卫,虽然由于担心高年级的打压和资历太浅,它诞生于1985年。已经大三的我们几乎都选在每晚十一点熄灯以后出动,一人一把吉他(不排除个别的是做样子),在楼下和楼道里或浅吟低唱《秋蝉》、《三月里的小雨》、《鼓浪屿之波》,或声嘶力竭地怒吼《一无所有》、《故乡的云》以及我们自己编的《你是一个天真的傻冒》、《我是注定了到处去流浪》。
这些深夜狼嚎,在很大程度上让低年级的学弟学妹们牙根儿痒痒让高年级的手心儿痒痒,为何?低年级的敢怒不敢言,高年级的已被分配和考研弄得无心求战。必须强调的是,这么说不是因为歌声很糟糕而是时间不恰当,可以想象:你正在想着“隔壁班的那个女孩”的时候,一群荷尔蒙充沛的男人高亢有力的“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这一吼还不把你憋死在被窝里!记得当年那首歌“你是一个天真的傻*,我跟你开玩笑,如果我要找你那也只是逗你,你可要千万不要当真,莫让那树上鸟儿笑你是不可靠,爱你丢下了我哦,爱你让我忘你忘也忘不掉……”是专门对付那些敢开门出来叫板的人。
如果当年有了卡拉、电子游戏和网络,我不知道我们的那段生活会变成怎样?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以群体形式出现的活动会少得多。记得是2000年前后,我和柱子夜入人大,在喷泉花园旁边还遇上了几个拿着吉他的人大教师子弟,攀谈中他们说当年在他们住的教工宿舍就听到过我们的歌声,还礼让我们来几句,柱子一展歌喉“亭亭白桦,悠悠碧空――”,那两小子敬佩不已:“您这是实力派!”
“哈哈,那是!”我告诉他们,我们那时候的声音是不“过电”的!
团刊
在人大我参加了合唱团、诗社和团刊编辑部的几个社团,多年过后,我仍然感激领我入门的师兄们。正是在这些社团里的锻炼,让我参加工作首选的单位就是做新闻工作并且很快上手如鱼得水。
想起来,还是非常嫉妒现在的小师弟师妹们,他们的互联网时代生活比起我们更加丰富多彩了。那时候要出一期团刊,仅是打字、校对、印刷,就需要十几个人忙一个星期,还记得有一期刊物的一篇稿件因为思想活跃被团委书记说有点“自由主义”,临出版时被抽下,为了不开天窗,我想找人画点插图,遍寻不着,最后只得自己拿着蜡笔(在蜡纸上刻字的笔,当年很盛行现在已经消失了)画了几幅画,哈哈,可怜我那拙劣的绘画水平!要是现在用电脑,怎么也可以搞点美女图上去。但这也成为迄今为止本人在印刷出版物上的唯一“艺术作品”。
那时候的宣传部长是高年级的老艾,东北人,脑子比嘴巴好使,为了笼络人心,也为了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他给每个团刊的负责人弄了一个小的工作证,红红的小本,就像学生证,我记得我的那本里面写着“校团委宣传部副部长、团刊编辑部主任”。那年寒假回家,我拿出来给外婆看,已经病入膏肓的外婆抚摸着那个小本,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工作,要对得起组织上的信任。如今外婆已经作古,那个小红本被我珍藏起来了,它记录了我的一段生活,有快乐,有苦闷,还有初为“领导”的新鲜和惶恐……
编辑部每年都招新生,最多时候我们的队伍有48人,主要是来自人大的新闻系、中文系、历史系等文学青年。盘指一算,现在这些人中有很多已经是大型新闻媒体的中坚力量了,我想他们应该记得这段经历,就像我永远不会忘记一样。
密云种树
“水平条”和“鱼鳞坑”,这两个词,既非计算机术语亦非地质学术语,是我们在1988年在怀柔水库种树时的专用词汇,都是当地种树农民告诉我们这些大学生每天要挖的两种树坑。
大概前后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从晚春种到了初夏,我清楚地记得离开时校车是从杨树光秃秃的枝丫中穿出城去的,而五月初我们回来时,几乎是被城里满目翠绿的杨树揽进学校的了(所以现在和将来,我始终会诅咒砍掉白石桥到中关村一路杨树的决策者们)。
那是一段艰苦但充满快乐的生活。
记得我们住的人大培训基地在一个叫金笸箩的的小村子,刚刚修建起来的基地宿舍,连地面都没有铺水泥,墙壁还是红砖,衣服掉地上就是一层土,吃饭和上厕所的环境就像农村一样。
这个镜头我一直认为很美:每天六点多,一群穿着既不像农民也不像学生的那孩子女孩子,有的还打着哈欠啃着馒头嚼着咸菜,从密云水库脚底下的几栋小红房子里出来,一些人扛着铁锹,一些人拎着丁字镐,顺着一条小河拖曳着往另一片山区里进发。我们从北往南走,那时的太阳比现在大而温暖,从我们的左边笼罩过来,群山一遍静寂,清冷的风在山谷间流泄,只听得我们的打闹声和吼叫声,40多人的队伍居然拉了一里多路,而歌声就断断续续地飘进了四周熟睡的村庄里,免费送给了那些还搂在温暖被窝里的密云农民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爬上云端,更接近那蓝的天,最高的山峰在眼前。脚下的弯弯流水,就像一串银项链,看一看山脚下,更接近那蓝的天。我们爬得高,我们望得远,把欢乐和美妙的心情散布在山水间……”
其实,就算是来自农村的同学,每天走几十里山路再干上几个小时的体力活儿,也受不了,何况这里面大部分是没经历过劳动的城里孩子?因此,每天收工以后的晚饭就是我们企盼的大餐,男孩子们总会凑凑钱买上点啤酒和葡萄酒,偶尔会有家境宽裕的兄弟们赞助几根红肠粉肠(那时候可没有现在丰富,什么啤酒肠、鸡肉肠、鱼肉肠统统没听说过,估计全中国都没有,可恨阿,现在这帮幸福的兔崽子们),每人上食堂打一个菜,哈哈,凑一起就只剩下幸福了。
记得我的一件糗事:时隔二十多年,实在记不清是我买的还是别人委托我拿的,那两瓶从离驻地几里的地方买的通化葡萄酒应该是当天晚餐的“催化剂”和“爆破筒”,我把他们装在外衣的两个口袋里,一路上双手捂住衣服,连当天的铁锹都是于水帮我拿的,这般小心呵护,只恨不得揣在怀里。路上大家说说笑笑,商量好了酒酣耳热之后约上有意思的几个女生上水库大坝去吹夜里的山风。一路上我也是紧赶慢赶,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跨宿舍楼前最后一道小水沟的时侯,我居然踩着了一块活动的石头,一个大马趴:咣当!酒液将我的衣服和地上染得鲜红……
想想也挺有意思,一块小石头可能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轨迹,那天晚上的酒没喝成,但他们还是上了水库大坝,我没去,所以我和班上女孩子的故事就提前结束了。要不然,谁知道班上哪一个倒霉的女孩子会摊上我?
“诗歌”情节
喜欢诗歌可能源于初中时看《五朵金花》电影和黄梅戏《天仙配》。那时候父亲在一个国营煤矿当领导,煤矿经常给那些累个半死的下矿工人们放电影,或者拉个戏班子过来唱几天大戏,电影和曲目就那么几个,四人帮下台了,样板戏刚被清理,这些都是带点浪漫主义的作品,当然看不腻也唱不腻。
七十年代末期,我那时候应该是十三四岁,属于情窦初开,最喜欢的就是《五朵金花》和《天仙配》。尤其是那里面的歌词,经常在黑暗中拿着纸笔“盲记”,回家再誊写好,然后上学校和同学一起练唱。记得那时候还时兴买一种小歌片儿,像扑克牌大小,几张联在一起,我可攒了不少。这样久而久之,对歌词的喜欢带来了我对诗歌的兴趣,大学进了中文系,自然免不了试试手。
第一首诗好像是作业,当代文学的老师还在课堂读了我的作品,什么“小河”、“浪花”、“眼眸”、“远方”之类的词儿(现在的小资类),我现在忘记了具体内容,但好像老师和同学当时反应还不错,哈哈,这可助长了我写诗歌的热情,此后一发不可收。在大二到大四,我参加了人大的诗歌协会、文学社,担任了《人大团讯》的主编,现在要说,那都是诗歌惹的祸。
大三时候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我以为是在恋爱,于是写了很多诗歌给她。她是外系低年级的,因为是文学青年,跑到我们团刊来应聘记者,一来二往就对上眼儿了。开始我们只是跑出去采访写稿,后来就出去看电影,然后就逛公园了。
她是个北京姑娘,漂亮大方,也很聪明,父亲是广东的,母亲是北京的,我给她写了一首《南方和北方的孩子》,应该是倾尽心力的。还记得最初的相识是她在谈她的中学男友如何如何欺骗了她,让我帮她“复仇”,结果在筹划复仇的过程中,她被我给俘获了,哈哈。可惜,这故事也就不到两年,最终我们还是放弃了(原因不表)。
记得最后一个学期,我们没怎么联系,她那时候已经有了新的男友,有一次同宿舍老段煮方便面把窗帘点着了,我们的床铺也陷入了火海,当天晚上,我们是坐在黑黢黢的床板上听着费翔《故乡的云》度过的。着火的第二天,一大早有人敲门,我朦胧中开门,看到一张红扑扑的脸,原来她从家里拿来了被褥给我,我好面子硬是不想要,她说:“这是我中学时睡的被子,昨晚我让妈妈找出来洗了的,你快毕业了,就别买新的将就着吧。”这一番话让我鬼斧神差地接下了,那最后的半年大学生活,我几乎每晚都浸润在她的气息里……
离校时,我不愿意打扰她的新生活,但又要和她说点什么,最后想的就是诗歌。正好诗社要搞一次毕业班诗展,死党于水给我在教学楼门口的橱窗里留了一个最好的位置,于是,我给她的最后告别也堂而皇之地公示于众了:
……
不想再看你的泪眼
不要再企望春天
只愿你昔日晴朗的笑脸
伴我浪迹天边
不要再说再见
我们不仅仅错过今天
当最后一阵鸽哨消失
那就是结局的语言……
兄弟们
我的兄弟就是中文83除我之外的20位男生。我们一起度过了将近1500个日日夜夜,彼此从陌不相识到耳鬓厮磨,从警惕隔膜到肝胆相照,有过误会、摩擦,拌过嘴也动过手,更有过理解、感动,一齐哭过也笑过。
毕业以后的今天,我好像格外珍惜这些兄弟,一些在校时不能理解的言行都成了记忆中很美好的东西。我上学时只和几位同学来往的比较密切,原以为其他人都是些没意思的家伙,或书呆子,或情种子,或身体比头脑发达,或心眼比头发还细。但这些年来,因工作原因东跑西颠,得以遍访各地诸侯,仔细接触一些人以后,我慢慢发现每个人其实都是一座富矿,都有很丰富的心灵和优秀的品质。
如同坐火车,我们刚好坐在了某一个座位上,一路上只和周围的几位聊聊风景人生,无暇顾及车厢里其他有意思的人们,更没有花时间去别的车厢走走,还以为上帝就是这样安排这段旅途的。其实,每一个座位都有有意思的话题和可爱的人,只因为我们的行程有限,倘若我们能走过去坐下来,或者仅仅是去驻足一下,倾听他们的谈话,看看他们的笑脸,就会发现一些美丽的东西,甚至因为与某个人的交往而在生命里留下难忘的记忆……
这使得我不免慨叹:年轻时,我们还不懂得如何判断一个人、如何和人交往。如同我们那时的爱情,以为对方一头长发、四科全优就是心目中的公主,看那些说话简单、做事爽快的就不愿接近,实际上,四科全优未必做得好家务内政,简单爽快没准就是出得厅堂、进得厨房的贤妻良母。
女人如此,朋友亦如此。
这是一列火车,没有预告终点,我们都只知道起点在哪里,而其中四年是共同走过的旅程,这段时间里,我们坐在了一起,看过同样的风景,听过同样的故事,虽然有各自不同的心情。
20年前我们分头下了车,就像一群小羊被撒在了草原上。这些年来,有的好吃好喝,有的受过饥寒,有的换过草场,有的回到家乡,但我们都还满足,都还快乐,这就要感谢上苍。
路还长,我们欢呼,大家还健康。
路还长,我们庆幸,40个兄弟姐妹都还在路上。
路还长,天还很亮,把你的手给我,把我的手给你,来,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去迎接那些还没到来的未知的风雨,去享受那些一定会温暖和灿烂的阳光……
(人大中文系1983—1987本科,现任中国民航集团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