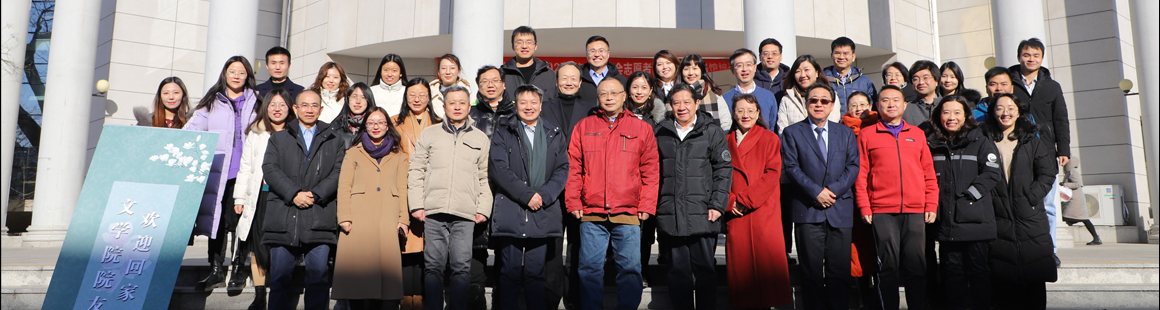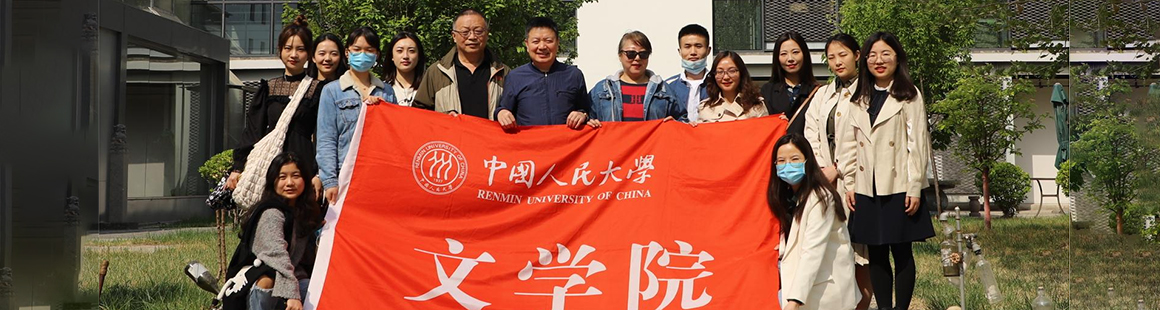【回忆录】宗金柱:浮生三记
发布时间:2010-05-31
来源:校友
浮生三记
宗金柱
转眼间,大学毕业二十载。我们在多梦季节经历的一切,被时光的筛子反复地过滤着,许多重要和不重要的故事已不再完整,但那些吉光片羽的有趣细节,却如断线的珍珠一般,永远散发着诱人的光芒。即便在“屏却丝竹过中年”的今天,我们的记忆也不会“事如春梦了无痕”,在走出象牙塔后天各一方的聚聚散散中,注定要延续我们今生的不解之缘。
校园记趣
1983年,四十名少年男女从天南海北走进中国人文科学的最高学府——中国人民大学,组成一个小集体——中文八三。这一年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七年,就在这一年,那些先结婚、后上学的“老三届”大学生中的最后一批人全部毕业了,大学校园里开始出现清一色的娃娃脸,从校门走向校门的我们,所有的骄傲与自豪都写在脸上。在当时的国内报章杂志上,我们被称为“天之骄子”,这种称谓绝无调侃戏谑的成分,有的只是真诚的羡慕和祝福。毕业多年后,我看到一个权威数据,说是当时全国所有大学的本科生招生总数,与现在的研究生招生数量基本相当,谓之凤毛麟角,绝不为过。
每个大学生宿舍都是故事最多的地方,我所在的学三楼316也不例外。我们宿舍总共住了七个人(后来补住了一位八四级的同学),其中五个同学和我一样是来自农村,宿舍人口的城乡比例是二比五,典型的农村包围城市,但在知识结构和经济实力上,我们这些农家子弟却是弱势群体,好在那时并无精神歧视一说,真正像宪法上说的一律平等。最初,在适应校园和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尽管处处感受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反差,但我很快就实现了脱胎换骨般的转变。记得刚刚入学时,第一次听别人用录音机偷偷放邓丽君的歌曲,我一下子惊呆了,心想这可是报纸上反复批判的靡靡之音啊,但第一个学期没过完,我自己就学会了很多港台流行歌曲,而且经常在水房和走廊里放开嗓子大唱,被戏称为“走廊歌星”,自我感觉还特别好。这一转变中隐含的复杂而微妙的心理调整,是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所难以体会的。
人到中年,现在已经很少唱歌,但每当我听到《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首歌,就会想起海鸥。海鸥姓庄,北京人,在316宿舍年龄最小,也最爱逗趣,我的绰号“柱子”,就是他首先叫出来的。起因是在班里举办的一次联欢会上,我即兴编了一个“鸽子飞到大海上”的谜语打趣他,谜底隐射他的名字——装海鸥,这个谜语引来哄堂笑声;作为报复,他在事后回敬了我这个亲切的绰号,一直从学校叫到工作后的朋友圈内,二十年长盛不衰,都拜老弟之赐。大学四年,我和海鸥的交往最多,几乎无话不谈,他的聪明和狡猾只在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为了逃避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他在毕业后娶了一个美籍华人做老婆,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海鸥在316的最大贡献是教我们几个南腔北调的人学会了普通话。记得入学第二天,他就自告奋勇地表示要对我们进行语言训练,在教诲我们的过程中,有时故意搀杂些市井的方言土语,比如形容女孩好看叫“盘儿亮”等等,来自河北唐山的刘树国坚持认为这是电影上坏人才说的话,打死也不肯学。经过海鸥的持续努力,我们几个乡吧佬不但学会了说普通话,同时也从他的讲述中领略了京城的风土人情,完成了最初的文明洗礼。只有一个人在大学四年内乡音未改——来自安徽桐城的汪志勇,无论他怎么努力,他的舌头硬是发不了卷舌音,大家不得不多数服从少数,每天吃早饭时,一律把大米粥叫作“大米猪”。
大学时期的趣事,要数一年级的时候最多。入学第一个学期,班里的大部分同学似乎都在一夜之间成了诗人,晚上熄灯后,每个蚊帐里都会燃起蜡烛,传出笔走龙蛇的“沙沙”声。一位高年级的老兄开玩笑说,每当新生入学,随便在校园里扔一块石头,都会砸着一个诗人。这话一点不假。我们316的老大于水当年在学校里比较出名,就是因为擅长写诗。初见于水,很奇怪这个东北汉子却长了一副清秀面孔,他不但诗写得有趣,而且非常有实干精神,毕业前,他凭着一己之力完成了《学院诗选》的编辑出版工作,自己一个人组编稿件,自己设计封面,跑印刷厂校对,事必躬亲,效率奇高。难得的是,于水对诗歌的热情一直从一年级延续到毕业前,更难得的是,他在工作后立刻把这份热情抛到了九霄云外,再也没有写过一首诗。那时,我本人也曾涂抹了不少分行的句子,记得入学后的第一个春天,全班到北京郊区的密云植树,我写了一首《唱给荒山的歌》,被一位老师推荐到校刊上发表了,其实这首诗的内容有些虚张声势。当时的我们,内心充满了八十年代所特有的激情和社会责任感。
当然,在禁欲主义处于尾声的八十年代,诗的主题也离不开爱情。有趣的是,当年的学生守则上堂而皇之地写着在校学生不许谈恋爱,虽然这样的规定限制不了胆子大的人,但对大多数人还是有效的,于是大家只好在诗歌中隐秘地表达对爱情的想象和向往,这样的诗在我们的班刊《小荷》上发表后,往往引来好奇的猜测。有一次上课前,317宿舍的马彤似乎从上面刊登的诗里发现了什么大秘密,当即站起来大声嚷嚷:“有人利用班刊谈恋爱啦。”他的促狭,令班里诗风一转,脸皮薄的人再也不写情诗了。
后来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不是马彤这种促狭的家伙一再干扰,堂堂中文八三绝不至于只出现一对恋人,孤独得像昆仑山上一棵草,子牙河上一根苗。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可以为这个推断做注脚。有段时间,我们宿舍的老汪和班里一位女同学交往较多,精明过人的马彤似乎窥到了什么端倪,他灵机一动,分别冒充老汪和那位女同学的笔迹,给两人各自写了一封信,“两人”在信中相约共游紫竹院公园。马彤这家伙多才多艺,字迹模仿得非常到位,老汪和那位女同学竟然信以为真,于是在某个周末的黄昏,两人在公园中漫步交谈时说到信件的事,才发现有人暗中导演了一幕“阴谋与爱情”,此时的马彤和其他几个男同学正躲在茂密的竹丛里笑破了肚子。随后,恶作剧被公布出来,老汪听了只是厚道地笑骂了一句:这帮坏小子。于是,一个想象中的爱情故事无疾而终。老汪在毕业前自豪地公布了他的恋爱对象——一位就读于安徽某所大学的漂亮姑娘,看了她的照片,我在老汪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兄弟八人居其三,家住桐城九华山,我有一愿君须记,娶了嫂子别忘咱。十年之后,当我在九华山上给合肥老汪家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正是她的夫人,我一报家门,她立刻大笑起来,说你就是那个写打油诗的柱子啊。
毕业前,每个人的去向已定,大家沉浸在依依惜别的气氛中,即便如此,我们也没忘了给自己找点乐子。那段时间,我们班的夜游神小乐队在学校里很出名,通常是每天晚上10点息灯之后出动,在校园里弹着吉他边走边唱,忧伤或快乐地发泄着过剩的激情。乐队的固定成员有老郑、马彤、王勇、于水和我,其他人有时也会也加入进来。那时,我们每天必唱的一首歌是自己作词作曲的,调子诙谐,甚至有点玩世不恭,每次唱完这首歌,必有路人报以掌声。有时唱到夜深,也难免会打扰别人休息,有一次,我们正唱得高兴,几个低年级同学走过来苦着脸对我们说:“大哥别唱了好吗,明天还要期末考试呢。” 毕业数年后,有次我和老郑回母校,在花园喷水池边遇到一群弹吉他的少年,趁着酒劲儿,我们吹嘘起当年的丰功伟绩,少年们立刻肃然起敬,说他们以前就听过我们夜游神的歌,并恭敬地递过吉他,非要我俩垂范一番不可,弄得我和老郑大窘,只好假装从容地说好久不玩手生了,才勉强应付过去。
老郑名学锋,住在对门317,我们是在毕业之前成为铁哥们的,毕业后更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关于他的趣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老郑也是著名的校园诗人,我最欣赏他的一首《大学生》,这首诗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把八十年代大学生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我至今记得里面有句 “走出去,我们就能澄清玉宇。”毕业后有次回学校,正赶上礼堂里举行文艺晚会,我们俩进去欣赏了一会儿,忽然看到著名表演艺术家瞿弦和走出来,他的节目正是朗诵这首诗,紧接着,一位女同学又朗诵了老郑的另一首《南方和北方的孩子》,当时,老郑坐在座位上那副得意的样子可想而知。
回想起来,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我们这些社会宠儿确实如老郑在诗中所调侃的那样,在时代的大潮中快乐而盲目地追逐着各种思想的浪花,满脑子里都是虚幻的雄心壮志,所思所为都散发着青涩橄榄的味道。真正认识到这青涩的可爱,是多年以后的事情。
江湖记缘
如果让我简短地概括自己大学毕业后的生活轨迹,大概只有四个字最合适——人在旅途。
毕业前,我原本被分配到某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秘书工作,但出于种种考虑,我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很多同学后来为我感到可惜,但我自己一点也不后悔。我从上高中时就向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生活,立志要当一名记者,这个愿望最终实现了。这一选择注定了我这二十年来的大部分时间要在旅途中度过,在一次次出差中饱览名山大川,也在各种各样的人生经历中广结诸缘。
说起来好笑的是,参加工作后不久,由于阴差阳错,我这个对摄影原本一窍不通的人竟做了摄影记者。我所在的单位是一家专事对外报道的中央新闻机构,从事新闻采访的自由度很大。除了拍摄新闻照片,我的另外一项工作是给香港、台湾的杂志提供图文专稿,曾经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笔名开过几个专栏。在日常工作中,我的采访对象可以说是三教九流,从政经要人、影视明星到小学教师乃至和尚道士,无所不包。我曾和老友郑学锋开玩笑说,我的工作可以称之为“上与王公同坐,下与乞丐同眠”,这句话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夸张,在我的新闻生涯中,既出席过场面盛大的国宴(有一次还因为工作误餐吃过江泽民主席个人掏钱请的阳春面),也在最贫困的农家用过餐,甚至在水灾、地震等突发事件采访中住过大车店……这些人生经历和精神体验,无论苦辣酸甜,都是值得珍惜的。
有几年,我曾担任专门采访中央外事活动的时政记者,个人名字被中央办公厅在“小名单”上备了案,每天忙忙碌碌地穿梭于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之间,在一次次拍照中近距离感受国家领导人的言行风采;我曾连续七年采访每年一度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并且是可以佩带A证上主席台的数名记者之一。从这些国务活动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明白了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自感受益非浅。
我还有幸亲眼见证了一些载入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如香港澳门回归盛典、建国五十周年大庆等。在台湾,我经历了新闻生涯中最紧张的一次采访,当时为了报道全台“三合一”选举,我在那里驻点一个月,在选举出结果的那一天,因为事先无法知道哪一方将胜出,我不得不紧张地独自穿梭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总部之间,幸运的是,我最终拍到了国民党庆祝胜选和民进党宣告残败这两个关键场面,当天,大陆所有的门户网站用的都是我的独家照片;当时,全台湾只有我一个来自大陆的摄影记者,我的报道在大陆摄影界创下了几个第一:第一个进入民进党总部,第一个公开发表台湾当局领导人照片……
因为工作的缘故,出差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有时一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外地度过,一路算下来,我用了不到十年就走遍了全国各个省份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我也经常有机会见到在各地工作的同班同学。1995年去新疆,我独自在长达两千公里的边境线上走访了生产建设兵团的许多农场,中间特意去看了段景华在一篇获奖散文中描绘过的赛里木湖,并在他上中学的边城博乐流连了数日,接着又无意中闯到了他的出生地精河县;因为时间紧张,我事先并没把自己的新疆之行告诉景华,直到采访结束后回到乌鲁木齐,我才打电话约他见面,为了留我多盘桓一天,景华强行让我改签了机票,以作长宵快谈,那种他乡遇故知的快乐真是没法形容。
出差久了,有时还会发生些无巧不成书的故事:1991年去杭州,我给地主徐斌打电话,他却告诉我海鸥也到了杭州,而且在我之前刚刚和他通完电话,我们两个竟象是相约而来;1992年随一个日本青年代表团去东北,在北京起程时发现同行的还有我们班的赵晨,我们俩在几天内一连走了沈阳、长春、哈尔宾三个城市,走马灯似地见了杨剑锋、于水、王勇;最有戏剧性的是1988年在贵州与郑学锋的巧遇,当时我正在机场准备登机返回北京,一抬眼看到老郑迎面走来,他乘坐的飞机刚刚抵达机场。这样的巧遇,令人不得不相信缘分的存在。
因为机缘巧合,我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了许多在学校时不太熟悉甚至并不认识的校友,我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结缘于喧嚣浮躁的90年代初,十几年之后,官场得意的升到了副部级,生意兴隆的成了大款,在艺术上成功的作了名人,不自检束的进了监狱,遭遇不幸的甚至离奇失踪了,其中一些人的命运浮沉,令人感慨系之。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了一个作地产生意的哲学系校友,并和他成为深交多年的铁哥们,通过他,我看到一个让我感到惊奇的现象,人民大学这个人文科学的最高学府,竟然出了不少商界人物,其中一个在一夜暴富后成了今天有名的地产商,另一个则在经历了一次重大挫折后背了一身的债,身边只剩下一辆为了面子而不肯卖掉的奔驰车。眼看着他们大出大进的豪举,以及彼此之间产生的恩恩怨怨和分分合合,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被那位铁哥们拉下水,他有很多次劝我放弃现有工作和他一起干,好在我有自知之明,始终不为所动,也正因为如此,才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保持了真正的友谊。
因为某个校友,我与大名鼎鼎的牟其中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牟虽然不是人大的校友,但在我们上学时,他就拉了一帮人大的在校研究生为他作生意撑面子。他在生意场上唯一的杰作就是用几十个车皮的土豆、衣物等生活用品从俄罗斯换回了四架飞机,气魄不可谓不大,他的名字曾经一度上了福布斯财富排行榜,可惜后来再没有作成一件大事,空有滚滚而来的银行贷款,却难以实施他那些大而无当的宏观构想,巨大的财富泡沫最终破裂。在他入狱前,我是最后一个采访他的记者,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在一个又一个催债电话的扰攘中,他亲笔为我写了一段文字,内容是介绍他的公司在俄罗斯发射了一颗并不存在的卫星。
二十载江湖,看惯人生的潮涨潮落,我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归结为一个缘字,也深深懂得了随缘,惜缘。
好古记愚
说起来难以置信,像我这样一个每天享用着现代文明成果的人,骨子里却藏着一个旧式文人的的传统情怀。即便在同班同学中,知道这一点的恐怕也不多。大学四年,我读的书中有一半以上是古代经史子集,这种偏好使我在外国文学方面涉猎甚少。我那时对古文的兴趣,只在三件事上有所流露:一次是入学第一个学期看了电影《火烧圆明园》之后,乘兴填了一首满江红登在校内诗刊《七色虹》上,那时的我根本不知诗词格律为何物;另一次是用文言写了一篇呼吁教育改革的小字报,善良的刘树国曾为我的举动表示担心,不料却得到了教古典文学的吴小瑜老师的赞赏;第三件事就是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古代隐逸诗初探》。
小时候,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乡村顽童,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的内心世界。上初中时,从老宅的夹壁墙里拆出线装的上下两册《唐诗三百首》,一读之下,立刻沉迷,我经常沉浸在虚无缥缈的诗境冥想中,村外河边的一片茂密树林成了我胡思乱想的天堂。有了这样一番陶冶,我的性情忽然变得斯文起来,不再无休止地淘气。可以说,正是那两本唐诗,造就了我今生难以摆脱的好古情结。
多年来,我的枕边离不开几本书——《史记》、《聊斋》、《唐诗别裁集》,即使出差在外也要带上一本。旅行之中,我对古迹的喜欢程度,也绝不亚于对自然风光的欣赏,在别人看来荒凉无趣的场所,我却看得津津有味,举凡佛庙道观,逢之必入,一看到古代装束的和尚道士就感到亲切,看起来他们似乎也很愿意和我交流。记得第一次到苏州寒山寺,该寺的方丈楚光大师一见我就丢下一帮求字的日本人和我攀谈起来,并当场书写了张籍的《枫桥夜泊》条幅送我。一位信佛的朋友听了我的故事,曾极力劝我皈依佛门作居士,其实我从不迷信任何宗教,但我承认自己很有佛缘,不然何以有机会与全国那么多名寺古刹的住持方丈们广泛结缘?这些人有的是在游历中偶然遇到,有的则是在全国政协会议主席台上有意结识,他们赠给我的佛门信物,大概可以办一个小型展览。
除了这些正教人士,我还接触到许许多多鱼龙混杂的奇人异事。在气功盛行的九十年代初期,那些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大师”们,大部分我都一睹真容,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总想弄清他们的所谓功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的结果是这些大师被现代科学一一揭穿。但张延生是个例外。有次我在办公室丢失了一台照相机,有位朋友向我介绍了这位预测专家,随后给了我一个他家的电话号码,电话接通后,没等我说几句,他就滔滔不绝地把有关照相机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最为神奇的是,他不但说出了我办公室的布局环境,就连我的办公桌挨着向阳的窗户也说得毫厘不爽,他甚至纠正了我记错的丢失日期;当时我和在一边旁听的同事感到毛骨悚然,直至今天都仍然觉得不可思议,特别是后来当我了解到张是一位曾在北京航空学院学过飞机制造的工程师时,更是增加了对他的神秘感。因为这件事,有段时间我对《易经》非常着迷,试图从中探究出什么秘密,最终只学得一些打卦批八字之类的游戏技巧。
我的好古情结时时作怪,还表现在其它一些方面。一个特殊的机缘,触发我写了百余首旧体诗。在外派澳门工作的两年间,南方的多雨天气和客中的孤寂,令我少年时所读的唐诗开始发酵,此时碰巧又在网上看到一个旧体诗词的论坛,遇到一批有相同爱好的人,他们在网上的名字千奇百怪,作品则玉灿珠辉。在与他们的切磋中,我彻底弄懂了过去一知半解的格律、韵部等等,写诗的技巧也大为提高。后来,我和这些网友成了现实中的朋友,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些喜欢老古董的人竟然是那么年轻,有的还是在校大学生,但一些人的古文功底之深厚,文笔之老辣,都让我自叹弗如。他们拥有自己的小圈子,每年出版一本集体诗集,时不时地组织象古人那样有趣的雅集,比如在端午节穿上古装祭祀祭屈原等等。因为写旧体诗,我还和台湾的著名作家张大春先生结下一段因缘。张先生在网络上看到我在台湾游览蒋介石故居时写的一首七律,似乎对诗中隐隐流露的对蒋介石父子的微词略有不同看法,于是步韵和了一首,发在台湾中国时报电子版和两岸的几个网络论坛上,并引起一阵争论。
有时我想,在当今这个以财富多寡衡量一切的社会,象我这种“今之古人”是不是很愚蠢很无聊?有位古人说:不作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信哉斯言。
(作者系人大中文系1983—1987本科,现任中国新闻社摄影部主任)